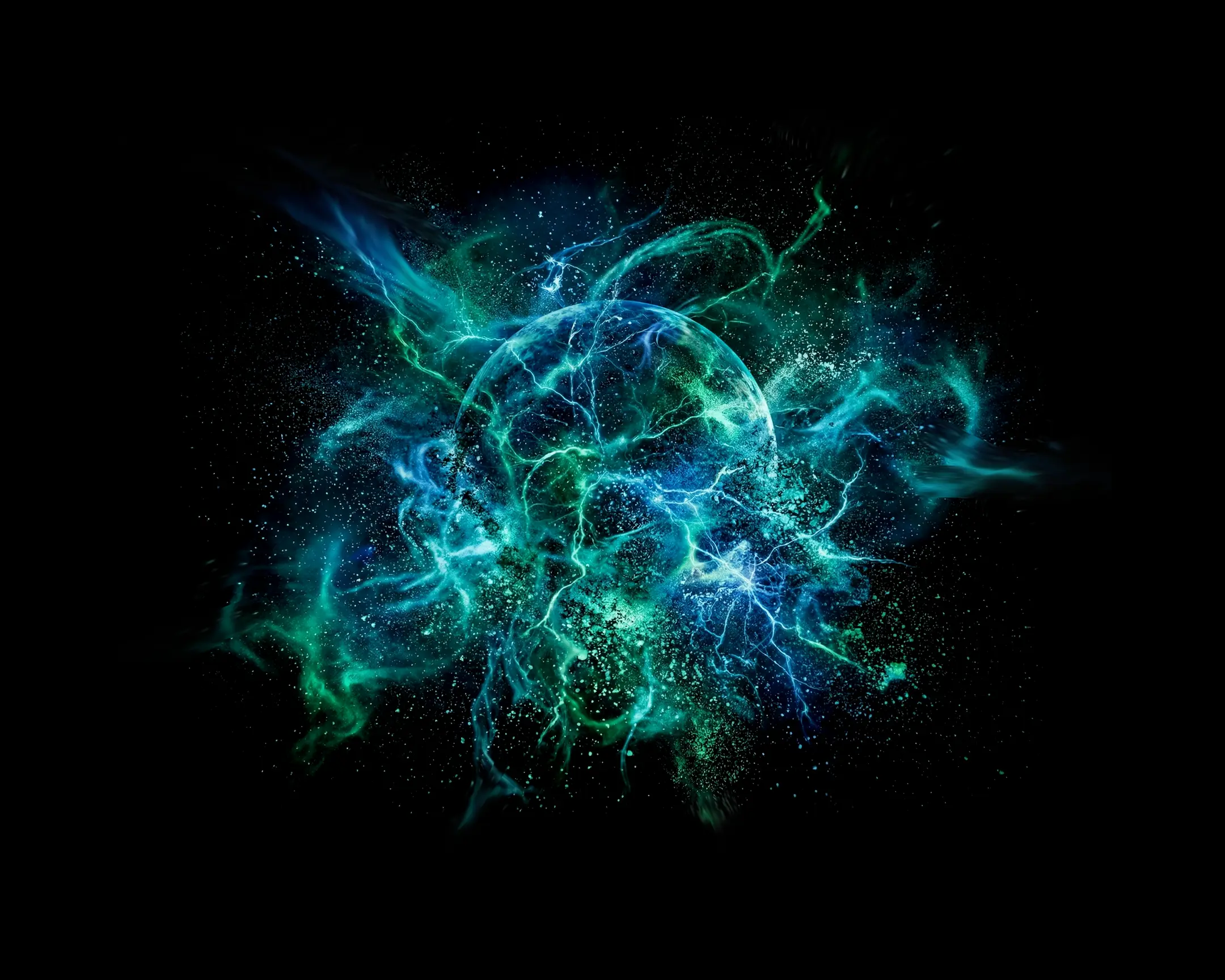
一、自由的悖論
年輕的時候,我很討厭進入某種框架和體制之中。所以選擇接案、選擇不進公司、選擇「自己決定工作節奏」—這一切看起來像是對體制的反抗,看起來又很帥。但自由有個詭異的特性:自由其實潛藏某種等價交換,在不知不覺中反噬。
當你怠惰多休息一陣子,會因為經濟、生存,開始無法選擇想接的案子;因為沒有經營曝光度,造成案源有限。「自由接案」變成「被迫接案」,以為逃離了框架,卻掉進了另一個更隱形的框架—經濟的框架。
更諷刺的是,現在要「主動」進入曾經逃離的體制,而這選擇本身讓自尊受傷。一方面是背叛了當初的選擇,另一方面是對自我期待的落空。
Claude提出一個觀點:真正的自由從來不是「沒有約束」,而是「選擇約束的權力」。 差別只在於:哪種不自由,對現階段的你更有利?承認這件事很難,因為它意味著承認 「純粹的自由」一直都是幻覺。
二、資本遊戲的必然性
有人會說:「我不想照資本規則走,我要做科學研究、藝術創作、文學創作。」,但這條路真的在資本之外嗎?
科學家要寫計畫書討好審查委員,爭取研究經費。藝術家要迎合畫廊品味,等待收藏家青睞。每一條看似「純粹」的路,最終都在某種形式上被資本吸收。 差異不在於「是否依賴資本」,而在於「目標需求」。
商業邏輯處理的是「已知的需求」—公司付錢是因為現在就需要你解決問題。學術、藝術處理的是「探索未知」—允許短期沒有回報的嘗試存在。但這個差異正在縮小:學術界看引用次數,藝術圈越來越商業化,文學市場更不用說。
所以問題從來不是「哪條路不在資本系統內」,而是「哪種成本、代價可以接受」。 所有選擇的道路都是價值交換。科學家用研究換經費,藝術家用作品換認可,你用時間換薪水。承認這個現實不是投降,是看清楚遊戲規則後,決定怎麼玩才對自己最有利。
三、探索未知 vs 螺絲釘焦慮
「進公司之後,我寫的code屬於老闆、產品屬於公司、成就屬於團隊。我只是一顆可替換的螺絲釘。」這種焦慮來自一個更深的需求—被世界記得。
插畫師有風格識別度,動畫師有作品署名,但前端工程師?寫得再漂亮的Vue component,用戶也不知道是誰寫的。你的貢獻變成無名的基礎建設。
我問Claude:「這些經驗和技術成長,自己做side project是不是也能獲得?為什麼一定要進公司?」。Claude認為:我要的不只是技術成長,我要的是確認「自身的存在有意義」這件事情。
但這裡有個邏輯陷阱:我把「意義」和「個人署名」綁在一起。如果我寫了迷因典的網站,別人不知道是我做的,但迷因典這個網站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有意義。意義不來自擁有權,而來自影響力。 錯把做有意義的事情跟名聲綁在一起,這才是真正卡住的地方。
四、公司經驗的真正價值
技術成長上,公司和side project的差異其實沒有想像中大。我自己也知道怎麼學React、怎麼寫Three.js。但公司給的三樣東西,是side project無法複製的:
第一,不同規模的經驗。 我的side project可能有100個用戶,公司產品可能有10萬、100萬。效能瓶頸、錯誤處理、edge case的複雜度是指數級的差異。只有在真實流量下,才能知道code會以什麼形式崩潰。
第二,協作的摩擦成本。 自己的專案自己說了算,公司裡要跟PM、設計師、後端、QA,甚至法務和資安協商。這是「在限制和妥協中仍然做出好東西」的能力。
第三,社會意義上的證明。 「某公司的前端工程師」vs「10個side project」,在下一個雇主眼中的可信度差很多。「有人願意付穩定薪水」本身就是一種可信的證明。
公司是效率極高的槓桿—用時間和自主權,換取自我提升的加速器。 當然可以靠side project累積同等經驗,但需要自己找流量、自己處理大規模、自己向社會證明。這很難,而且很慢。
五、螺絲釘的高矮胖瘦—工程師的「帥」
我覺得前端開發沒有風格識別度,不像插畫那麼有個人標誌。但這是因為還在「使用工具」的階段,而不是「創造工具」的階段。
Evan You是前端工程師,他創造了Vue。Dan Abramov是前端工程師,他創造了Redux。Sarah Drasner是前端工程師,她定義了動畫CSS的美學標準。他們都有強烈的個人風格,只是展現方式不同。
工程師的個人性不是依賴「獨特性」,而是「可靠性+美學」。那個把複雜動畫做得又順又美的人、那個code review總能抓到關鍵問題的人—都是風格,只是不像插畫那麼視覺化。進公司不是當螺絲釘,而是在高難度環境裡,證明我的方法論是可行的。
在side project可以做任何酷東西,但沒人會挑戰「這個在10萬用戶下會不會崩潰」、「這個維護成本是不是太高」。公司是殘酷的試煉場—如果在嚴酷的環境裡仍然能寫出優雅、高效、可維護的code,那也是一種帥,只是需要改變對這個帥的描述方式。
結論
生而為人,就是被拋入一堆限制裡:身體會老、需要錢、需要認可、需要意義。我沒有選擇要不要出生的權利,也沒辦法跟玩遊戲一樣選擇起始條件。生命這件事情本身就荒謬。
卡繆說唯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,那就是自殺與否?—意識到存在的荒謬後,還要不要繼續玩這個遊戲?我的怨懟其實就是這個:「靠北,為什麼我要被迫玩這個我沒同意的遊戲?」。 這個怨懟不會消失,也不該消失。它是意識到自己處境的證據。
但承認荒謬之後,還是得決定怎麼玩。問題從來不是「哪條路不在資本系統內」,而是「哪條路讓你覺得,即使在玩這個被迫的遊戲,你仍然玩得夠帥、夠有尊嚴」。 所有選擇的道路都是價值交換,所有自由都是有限的,所有意義都是自己賦予的。以現階段來說,我自認為生命的意義來自影響力、在世界這個大水池造成的波瀾。 相信有一樣疑問的你也能找到自己的生命意義。